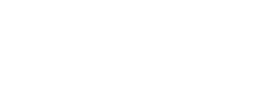一、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置实质上提供了罪轻辩护空间
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罪的基础上多加了“协助”二字,由此可以看出该罪主要规制的是帮助组织卖淫活动的行为。既然刑法总则有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对于帮助组织卖淫活动的行为人就应当以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进行认定和处罚。而刑法将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予以规定,属于一种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考量。在这里,笔者不禁思考: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该罪名的设置诟病颇多,但其量刑范围毕竟在组织卖淫罪之下,如果是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充其量也就是将其作为从犯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在情节程度相似的情况下,刑期高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最高刑期。因此,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置为组织卖淫活动中发挥其他外围、边缘性作用的行为人提供了责任减轻的可能性。故而必须好好分析其中蕴含的刑法基础理论知识和立法原意,以充分运用该罪名的规定寻求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的处理结果。
(一)“组织”内涵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具有高度黏连性,作为一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罪名,构成该罪名的行为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应当起到比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更小的作用。换言之,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人不能起到“组织”的作用,而只能是对卖淫活动的开展起到一些无任何支配作用的帮助效果。因此,即使从整体行为来看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都属于帮助犯这个宏观范畴,但这种帮助的性质和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否则,刑法也无需对这两种情况做出罪名和量刑上的区分。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组织卖淫罪的从犯都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而只有其中起到部分非组织性帮助作用的行为人才能够成立协助组织卖淫罪。行为成立协助组织卖淫罪必须符合不带任何“组织”作用的外围帮助性质,在明确这一点后,界定“组织”的具体范畴就成为了关键问题。
(二)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
由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关于组织卖淫罪的规定为简单罪状陈述,并没有过多的涉及具体内涵。因此,两高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认定为“组织他人卖淫”,也就是对组织卖淫罪的含义作出了明确规定。招募、雇佣等属于手段行为,而最终指向的目的行为“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才是“组织”的本质意义。即考量行为人是否有“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关键看其是否对卖淫人员产生了管理权和控制力。
学者张康之、李圣鑫在《任务型组织设立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组织要素分为人、事、时、财、物。”这对我们认定“组织”的具体内涵有重要借鉴意义。根据卖淫活动的相关运作机制,一般在组织卖淫活动的团伙中通常具有较为体系化的组织成员(比如总负责人、联系人、运送人、招募人等)、运作模式(如纠集卖淫人员的方式、宣传并吸引嫖客的手段)、资金流水(如接收嫖客的付费、给卖淫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支付工资等)。在以上这些要素中,可以区分出哪些事项是具有决定权的事项,哪些具有决定权的事项支配和控制力比较强,哪些事项涉及的范围广、人员多,从而认定属于“组织”还是“协助组织”。如果是对于整个卖淫活动的组织、策划、运营、开展架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就应当认定为是具有“组织性”,而如果是职责可以随意被替代,不论工作与否都不会对卖淫活动整体框架产生实质影响的,就不能认定为具有“组织性”,而充其量只能说是具有“协助组织性”。
二、协助组织卖淫罪和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区分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一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仅仅只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募集、联系卖淫人员和嫖客,按照上级的要求发布宣传、广告,对卖淫活动的发生和持续没有任何控制可能性,就不能认定该人的工作内容属于“组织行为”。而如果一人虽然并非直接决策者,但能够在微信群、QQ群内批准卖淫人员的请假申请,即使其并非核心组织成员,也可以认定其工作内容属于卖淫活动中的“组织行为”。是否具有管理和控制性的“组织行为”是区分协助组织卖淫罪和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关键。这种观点在《解释》第四条得到了印证: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作者原创配图
也就是说,尽管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中都有“招募”等手段,但行为方式并不能完全决定此罪与彼罪的定性,而应当综合整体情况进行考虑。如果只是单纯的为组织卖淫者招募、运送、代聊相关人员,对卖淫活动的开展不起任何实质性决定作用,而只是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就有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认定空间。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之区分界限也就在此。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尽管也是起到帮助性作用,但这种辅助行为能够体现对于卖淫人员的部分控制力。在具体辩护过程中,应当综合行为人从事的具体工作,从组织卖淫活动中获取的奖金、分成,是否有收钱、付款行为,次数和金额的多少与大小,参与时间长短,招募人员多少和成功率,等等情况进行认定,合理判断行为人对于卖淫人员有无控制力和支配影响力,属不属于发挥了“组织”作用。如果研究在案证据材料后,以常情常理常识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具有外围性,就应当敏锐地挖掘各种证据细节,以证明行为人没有任何管理和控制卖淫人员的能力,从而达到以轻罪认定、轻刑处理的结果。
三、协助组织卖淫罪也有主犯、从犯之分
既然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将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单独拿出来作为正犯对待,那么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否也存在主从犯之分?笔者认为是存在的。尽管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刑法总则的总揽性和原则性是每个法律人的共识。刑法分则无论怎么进行修订,都必须符合总则的框架和内涵。不论是否存在正犯化理论,协助组织卖淫罪作为一个独立罪名,就要受到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协助组织卖淫罪同样具有主犯和从犯之分。前文已经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两罪在客观行为方面的区别,在对“组织”和“协助组织”两种行为进行刑法评价时,由于适用具体行为范围已经存在差异,认定主犯和从犯也应当在各自语境下进行。
四、协助组织卖淫罪从犯是最佳罪轻辩护方向
在确认了协助组织卖淫罪有主从犯之分后,如何认定该罪名的从犯也是有效为当事人进行罪轻辩护的重点。对于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外围帮助的行为来说,同样存在相应内部分工。如果某些行为人负责与组织卖淫的上级进行联络,接收发布招嫖广告信息、纠集相关人员、代聊等指示,全面负责并管控卖淫人员的招募和运送,其余“手下”都听从其安排,那么在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范围内,这些起统领作用的负责人就可以认定为主犯。而其他只是听从安排,机械完成交派给自己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应当认定为从犯。举个例子,现有一人为运输卖淫人员的专职司机,判定其在协助组织卖淫中所起的作用,应对协助活动进行通盘分析。
具言之,运输车辆是否为该行为人准备的?该行为人对整体组织卖淫活动的流程有没有了解?是否只是单纯按照要求将人员从起始地运载往目的地?对非法获利的分配是否具有相应控制权?分得数额占总体协助组织卖淫行为非法获利的比重高不高?如果该行为人使用的运输交通工具为他人提供,并不清楚卖淫活动其他相关人员和具体程序,只是接收指令将特定的某人或某些人运送到特定地点,获得工资完全处在被支配地位,所得数额与起协助作用的他人相比较少,就可以认定其在协助组织卖淫中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成立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从犯。
因此,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应当综合组织卖淫活动的整体进行考虑,如参与时间有多长,涉案金额和获利数额有多少,招募人员的数量,具体工作内容等,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充分实现最佳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