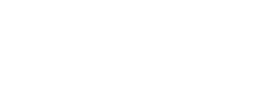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
今年以来,随着“扫黄打非”部门的主动出击,很多足浴店、按摩店和会所等涉黄场所都被查处,相关涉案人员也被抓获。在我所办理的一组织卖淫案件中,笔者发现有一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即卖淫场所中出资股东的刑事责任应如何认定?
通过查找相关案例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卖淫场所中出资股东扮演的角色五花八门。有些负责安排、调度和管理卖淫活动;有些虽是股东,但实际并不参与经营管理;还有些本欲退出是非之地,但因其他原因退股失败,仅顶着一个股东的名头;更有甚者对场所是否卖淫都不清楚。而对此类股东刑事责任的认定差异也较大,相似的行为有法院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也有法院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或容留卖淫罪。
由此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参与经营管理与否是否会影响行为人的罪名认定?有股东身份是否一律认定为组织卖淫?这一系列问题均是影响行为人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
二、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和容留
卖淫罪的界定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区分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争议,而要探讨卖淫场所中股东的刑事责任,首先要对相关罪名的概念和界限加以明晰。
首先,组织卖淫必须要体现“组织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 号)(以下简称《卖淫案件司法解释》)第1条中明确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是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虽然组织卖淫罪也包括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存在法条上的竞合,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组织性”的实质判断标准是行为人有无实际管理或控制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这也是与其他罪名进行区别的关键所在。在司法实践中,“组织性”又通常体现为决定设立卖淫场所,规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利润分配,对卖淫人员考勤、请假、奖惩进行管理等行为。
其次,协助组织卖淫作为组织卖淫的帮助行为,行为人并不从事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而是在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提供相关的帮助。在对两者进行区分时,笔者曾写过相关文章探讨(具体可参考:周立波《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区分认定——以李某组织卖淫案辩护为例》),认为不能因行为人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经理”等身份就直接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而应从行为分工入手,考察其是否对卖淫人员的卖淫活动具有管理、控制性,管理和控制性体现为对卖淫人员卖淫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而不是其他。而根据行为人在组织卖淫或协助组织卖淫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小,则可以进一步区分主从犯。
最后,容留卖淫指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的场所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的行为。容留卖淫的行为方式较为单一,即提供卖淫场所,行为人既不参与卖淫活动的管理和控制,也不参与招募人员、充当保镖、管理账物等帮助行为。因此,相比于组织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其在整个卖淫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较小,行为危害性较低,在刑罚种类上也增加了较轻的拘役和管制。
三、常见情形及定性分析
根据卖淫场所中股东的不同参与程度,笔者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情形分别探讨:
第一,股东明知店内涉黄,且参与相关经营管理,扮演着“拿钱又管事”的角色。比如在李某、范某强、任某海等人组织卖淫罪二审刑事案中,任某海作为足浴店股东之一,与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在足浴店提供卖淫服务,共同商议足浴店经营、决策以及核对确认每日账单,并约定了各自分工、分成,使得卖淫活动均处在股东任某海的监管之下。对此种情形,行为人作为卖淫场所和卖淫活动的实际所有者、控制者,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并无争议。
第二,股东明知店内涉黄,日常不参与卖淫场所的具体经营管理,但却参与卖淫活动的相关决策,通过雇佣员工负责卖淫场所的经营运行,扮演着“管大不管小”的角色。比如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268号方斌等组织卖淫案中,方斌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卖淫活动的具体事务管理,但其聘用彭建智担任总经理,管理卖淫活动。此类股东表面上退出经营管理,但在背后仍控制卖淫活动的整体走向,实际并未放弃对卖淫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权,对此也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
第三,股东明知店内涉黄,不参与经营管理,但参与分红,扮演着“拿钱不管事”的角色。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中,对于此类股东刑事责任的认定均存在较大争议。比如在唐某等人组织卖淫案中,于某3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提供卖淫场所,还以提供的房屋作为出资占有会所30%的股份,但其并不参与会所的组织、管理,法院最终认定于某3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吕某辉、胡某某等组织卖淫案中,被告人胡某某投资之初是为经营合法场所,后他人将其转变为卖淫组织,其虽没有参与该卖淫场所的经营管理,但参与了分红,知道后仍默示、容忍该卖淫场所从事卖淫活动,法院最终认其构成容留卖淫罪。虽然此类行为有法院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或容留卖淫罪,但在司法实践中更多因“股东”“出资”“分红”等因素,认定行为人为组织卖淫罪的共犯。
到底如何认定“拿钱不管事”的行为,离不开对“组织性”的评价。笔者上文中界定的“组织性”的判断标准,其实在实践中早已得到认可。《刑事审判参考》第78号高洪霞、郑海本等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中认为,组织行为表现为建立卖淫组织、对卖淫者进行管理以及组织、安排卖淫活动。第1268号方斌等组织卖淫案中也明确,组织卖淫认定的关键是行为人对卖淫活动有策划、指挥、管理、控制、安排、调度等组织行为,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已经形成有效管理与控制。也有办案法官表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就是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其所从事行为只能是与控制管理卖淫人员及卖淫活动无关的其他事务。
笔者认为,对于“拿钱不管事”类的股东,实际上为他人组织卖淫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对此应考察股东不同的出资目的和资金用途,分别加以认定,而不是一概以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如果投资入股的资金用于卖淫场所,那么股东在整个卖淫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仍仅限于场所上的帮助,则应认定为容留卖淫;如果投资入股的资金用于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打手、保镖、管账人等,那么股东仍只在外围协助组织者实施,则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如果投资入股的资金用于卖淫人员的卖淫活动,那么股东此时已通过出资对卖淫活动产生实质控制和影响,则应认定为组织卖淫,同时考虑其作用的大小可以区分主从犯。
第四,股东明知店内涉黄,但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参与分红,仅顶着股东的名头,扮演着“不拿钱不做事”的角色。比如在胡某宏组织卖淫案中,被告人胡某宏在得知浴场存在卖淫活动后,与赵某武口头协议,欲转让股份,赵某武同意转让款用浴场后期分红支付,但因其他股东不同意未能实际履行,之后胡某宏将工作交接给赵某武,其不再参与浴场工作。该案中,胡某宏主观既没有组织卖淫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也未对卖淫活动实施管理、控制行为,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此外,胡某宏出资行为在场所涉黄之前,其收取的分红实际是赵某武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可见胡某宏主观上也并没有协助组织卖淫的故意。但其既然未退股成功,作为浴场的股东在知道店内有卖淫行为后就有阻止的义务,其主观上放任浴场内的卖淫行为,客观上为卖淫活动提供了场所,可认定为容留卖淫罪。
第五,股东并不知晓店内存在卖淫活动。此种情形往往是股东在刚开始出资时店内并不涉黄,但后期店内开始提供卖淫服务,有些股东却并不知情;又或者股东在出资时并不知晓店内涉黄。此类股东因为并不存在犯罪故意,所以不构成犯罪。
四、结语
在理论和实践中,如何认定卖淫场所中出资股东的刑事责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实践中,因行为人“出资股东”身份,直接认定其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做法有失妥当。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首先要具体考察其是否实施了组织行为,有无实际上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其次,对于不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则要看其主观上是否有相关犯罪故意以及出资的目的、用途。如果股东明知店内涉黄,虽没有具体经营管理,但出资是为卖淫人员的卖淫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可构成组织卖淫罪;如果股东出资是为卖淫场所的买卖、租赁提供支持,则可能构成容留卖淫罪;如果是为雇佣保镖、打手提供资金支持,则有可能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办案律师仍要具体审查案件细节,实现对相关行为的准确认定。
参考文献
[1] 黎宏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295页。
[2]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4刑终260号刑事裁定书。
[3]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书。
[4] 惠东县人民法院(2017)粤1323刑初799号刑事判决书。
[5] 聂昭伟:《组织卖淫罪裁判观点十一则》,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 年第 24 期。
[6]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11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