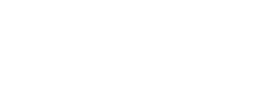承办律师:魏巍
2015年8月的一天,烈日似火。温州一位律师同行发来微信,说有个贩卖、运输毒品的二审案子,被告人A在一审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想推荐给我。
后来,家属从温州赶到了杭州。见了面之后才解到,家属从湖北老家赶过来,来的是A的父亲、叔叔和舅舅。
我们看了一审判决书,A帮助B贩卖、运输毒品,涉案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公斤多,而且A还有帮助B管理毒资的行为。从A的供述及其他证据来看,定罪量刑的依据很充分,又考虑到实践中二审极低的改判率,保命的希望很渺茫。
我们向家属如实谈了对案件的看法,家属却没有放弃的意思。A的父亲说,一审的时候,虽然家里知道她因为贩卖毒品被抓,但是从公安承办人那里了解到A的事情不大,最多被判个几年。所以,家里没有给A请律师,想着让她坐几年牢,好好反省反省。一审开庭的时候,家属甚至都没来旁听。万万没想到的是,A被判了个死刑立即执行。家属知道后慌了神,千里迢迢从老家赶过来。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只好通过一审的法律援助律师,找到我们。又得知我们所专门办理刑事案件,对我们很快有了信任。虽然希望渺茫,但家属说:“我们只想努力一把!”
“女毒枭”的第一印象:
接受委托后,我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承办法官取得了联系,及时复制了案卷材料。在阅卷过程中,我仔细查看了一审的庭审记录,发现A俨然是一幅“死不悔改”的“女毒枭”形象。公诉人问A:“你以前在公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A答:“属实”;公诉人问:“你跟B是什么关系?”A答:“情人”。公诉人问:“你有没有告诉B最近打了多少钱进来?或者把钱给谁了?”A答:“没有。”公诉人问:“为什么微信信息显示你一直向B汇报卡里的钱的情况?”A答:“不知道。”公诉人问:“这期间卡里有多少钱?”A答:“不知道。”公诉人问:“你每次过来都有带箱子?”A答:“最后一次带了箱子,但是是我的衣服。”公诉人问:“你原先供述,第三次来的时候带了毒品,你怎么解释?”A沉默不语;公诉人问:“你跟B微信联系一直有讲到毒品的事情,怎么解释?”A又一次沉默不语。
A在侦查阶段有过多次有罪供述,在一审庭审中,又反复无常,前后不一。要么狡辩,要么沉默。拿什么拯救你,“女毒枭”?
她有令人同情的坎坷经历:
阅卷之后是会见。见到A的第一眼,竟然是一个邻家女孩的模样,跟想象中的“女毒枭”的模样差距明显。我向她介绍了自己,介绍了她父亲如何找到我,转达了家里人的关心。她竟毫无征兆的哭了出来。一边啜泣一边说,一审期间,她无法联系上家人,家人也不曾联系她。开庭的时候没见到一个亲人,她在法庭觉得无依无靠,脑子一片空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让她绝望得只能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谈到案件事实,她说201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B。B比A年长不少,出手大方,对A展开了追求。一开始A只知道B是吸毒的。后来,才发现B有贩卖毒品的情况,一气之下,A离开B。离开后,A在东莞一家工厂打工挣钱,恢复了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 2014年5月份左右,B又一次找到了A,请A吃饭,给A零花钱用,甚至给A免费吸食毒品。无微不至的照顾,无忧无虑的生活,让A有些沉迷。在B的诱惑下,A辞掉了工作,住到了B租的房子里。A逐渐发现B是个极其敏感、警惕的大毒枭。在生活中,A必须对B惟命是从,稍有不从就会引起B的怀疑和警惕。B经常对A说:“帮我带点毒品,不会有事情的。毒品都是我的,即便你被抓住了,也跟你无关”。A文化程度不高,社会经验缺乏,竟然对B的话深信不疑。于是,B让A到瑞安办银行卡,A觉得不管这个卡用于什么目的,都跟她无关;B让A转发银行卡的短信,帮助转账,A也觉得与她无关;甚至B让她运输毒品,A也认为如果毒品是B的,即便被抓住,也与她无关。B正是抓住了A无依无靠、贪图享受又天真无畏的弱点,使A成为往返与深圳和温州之间的毒品运输“工具”。
对于父母,A有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从小父母对她管教严厉,她变得非常叛逆。16岁便辍学到工厂打工。打工期间,谈了个男朋友。她父亲发现后,把她关在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A对父亲产生了恐惧和恨,跟着男朋友私奔,在外飘零了三年。三年后,A带着男朋友回家,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结果仍然被父亲拒绝。她再次离家出走,男朋友又与她分手。这时,B出现了,给了A无微不至的照顾,让A找到了久违的被照顾的感觉。
过往的经历,让A对父母的恨大于爱。而一审期间父母的冷漠,使她彻底绝望。会见她时,我有意识的劝导她,把父母对她的关爱转达给她,让她重新认识到父母一直以来对她的关怀和期待。经过多次的会见和开导,她终于又拾起了希望,对未来有了期待。
把我们知道的故事讲给法官听:
通过阅卷,通过会见A,辩护思路逐渐清晰。在A已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二审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命。如何保命?除了要找出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也要让法官看到案卷材料之外的A。需要有人告诉法官,A并不是案卷材料中反映出的“女毒枭”形象,而是一个值得惋惜和同情的人。所以,二审辩护的思路很明确,一是告诉法官案件存在什么问题;二是告诉法官A是什么样的人。
案件存在的问题很多。
第一,一审判决认为A受B的指使到瑞安办理银行卡,用于毒品交易,并且还认为A对卡内的资金具有管理的行为。但是证据材料显示,银行卡办好之后,A没有事实上的管理行为,她对卡内资金的来源、数量、组成、用途、盈收状况等都不清楚,她仅仅按照B的要求有转发短信、转款等帮助行为。证据材料还显示,银行卡的大部分操作是由B本人完成的,且B对银行卡的资金具有绝对的支配权。第二,一审判决认定A三次运送“大宗毒品”给C,并且认为C家里搜到的4公斤多的毒品都是A运送过来的。这一认定也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A一直不知道自己每次运送毒品的种类和数量,毒品都是B事先包装好,放在箱子里后让A运送。其次,A在笔录中猜测的毒品的种类与C家里搜到的毒品种类是不相符的。最后,C是在A被抓半个月之后才被抓获的,在这半个月内,不能排除其他人继续向C运送毒品的可能性。在这些问题的指引下,通过分析A和C两人的供述、分析毒品的包装、毒品的销售、运输的频率等七个角度,来论证A每次运输的毒品不可能达到“大宗”的程度。第三,一审判决认定A对C卖给黄某的300克毒品承担责任,也不能成立。该笔毒品交易发生在A办理银行卡之前。虽然黄某是将毒资打到了A办理的银行卡内,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当时A知道银行卡用于毒品交易,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转发短信,向B汇报的行为。所以,从主客观来看,A不应该对该笔毒品交易承担责任。第四,一审判决认为A属于主犯,但是从A在本案中的主观认识程度、参与程度等方面来看,认定为从犯更加恰当。第五,综合全案的情况来看,A没有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严惩”的程度,不应该对A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除了案件存在的问题,如何让法官对A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有讲究。如果让A在法庭上自说自话,法官恐怕难以相信。需要让法官通过多种途径,对A进行了解,最好在开庭之前,让法官对A有提前的了解,加深法官对A的印象。所以,在开庭之前,我让家属先给法官写了封信,将A在家人面前的形象展示给法官;在开庭时,让A将自己的经历讲给法官听,让法官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在开庭后,我自己也给法官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多次会见A以来的印象和感受。三个主体,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对法官讲述A的故事。自然而然,法官对A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在法官的心里,A已经不是证据材料反映出的冷冰冰的形象了。
一审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
2016年1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宣判,其余被告维持一审判决,唯独将A的量刑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兴奋之余,也让我对辩护工作有了更多的思考:一成功辩护的第一步是让法官对公诉人所举的法律事实产生动摇。法庭上的法律事实,永远是用证据支撑起来的事实。辩护工作的基础永远是分析证据,剖析事实。公诉人用证据搭建出一个事实,说被告人做了这个事,是有罪的,请求法院定罪量刑。如果能够证明公诉人用存在问题的证据搭建出了一个错误的事实,那么将直接影响法院的审判。所以,律师取得辩护效果的关键,是能够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认定的事实提出不同的意见或举出相反的证据,动摇公诉的证据基础,进而撼动指控的事实。最终的目的,是让法官对指控的事实有所动摇,有所思考,最终难以认同指控的事实。二成功辩护的第二步是让法官将其动摇坚持到底。有人说,被告人的杀与不杀,往往就在法官的一念之间。就A这个案件来说,涉案的毒品数量非常巨大,A也参与了大部分行为。如果二审维持一审判决,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最终是什么促使法官进行改判?也许因素很多,但是从辩护人的角度来说,将辩护的范围扩展到涉案事实之外的领域似乎也是促使改判的重要因素。从案卷材料及一审的开庭情况来看,A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女毒枭形象。如果二审仍然给法官这样的印象,最终的可能性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二审的辩护策略是让法官看到不一样的A,让法官的内心产生怜悯和同情,这对案件的改判不能说没有影响。举一反三,在其他案件的辩护中,是否也能够调动其他积极的因素,去影响法官对被告人的看法,再结合证据及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最终让法官坚定地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处理,不失为一种有效辩护的策略。三成功辩护的最后一步是让爱回归,让恨泯灭。作为辩护人,除了找到案件上的问题,就案论案外,还应当有人文关怀精神。本案中,A与父母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存续多年。如果律师不从中予以劝导和协调,也许双方永远都不会有敞开心扉,再次相互接纳的一天。如果案件辩护成功了,却唤不回双方的亲情,将永远是律师的遗憾。所幸,在我的工作中,没有遗漏这一点。A有了蜕变,她在看守所中所写的一篇《妈妈,我错了》流露出了她对父母所有的愧疚,希望重新回归家庭的热切期望。她在庭审最后,被法警带离法庭的那一刻,对父亲喊出的“爸爸,我错了”,也让其父亲彻底撇开了过往的不快,开始重新接纳改过自新的女儿。也许,他们再一次一起生活,是在几十年以后。但是他们的内心,已经开始了共同的新生活。这一点,比辩护的成功更让我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