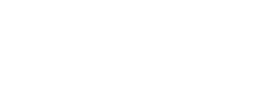一、一杯“隔夜水”与一起“放火案”
(一)一杯“隔夜水”
几年前,当笔者还在金华执业时,有天晚上11多到家后,因第二天一早还要出差,加之笔者有起床后马上喝水的习惯,遂,在睡觉前笔者倒满了一杯水放在餐桌上,准备第二天起床后直接饮用。可是第二天清晨(6点左右),当笔者起床后发现,昨晚倒满水的杯子变得空空如也。一问才知道,是笔者的父亲把杯中水给倒了,接下去就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我:老爸,我餐桌上的那杯水呢?
爸:我给倒了。
我:为什么给倒了?
爸:隔夜水不能喝的。
我:啊?为什么隔夜水不能喝?
爸:隔夜水不好的。
我:隔夜水哪里不好了?
爸:反正就是不好,不能喝的,你换杯新的呗。
我:(心理活动)靠,莫名其妙把我水倒了,让我喝刚煮熟的水,我怎么喝得下去?
笔者此时很困惑,如果是因为水放了时间太长,可能积累了有害物质,那么为什么喝桶装水,好像就没什么问题;加之,也没有什么科学研究表明放了几个小时的水就会自然堆积大量有害的物质。那“隔夜水不好、不能喝”的结论是怎么得出的?
读到这里,部分读者可能会困惑:“隔夜水”和“放火罪”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将这两个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告诉笔者,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的“隔夜水”现象,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二)一起“放火案”
前段时间,笔者同事参与了一起放火案的庭审,同事回来后和所里的小伙伴们吐槽了如下故事:
同事:今天这个案子开庭开得太郁闷了。
我:怎么了?
同事:庭上公诉人说:“《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行为犯,只要点燃了物品,物品独立燃烧了,放火罪实行行为就实施完毕了,放火罪就既遂了。”
我:那你怎么回应的?
同事:我说:“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点燃了一张纸,放火罪就既遂了?”
我:这个例子比较典型,但是放火罪是行为犯?恐怕公诉人的说法有失偏颇了吧。
同事:更郁闷的是别的事情。
我:哦?什么事情?
同事:开完庭后,法官说:“我们这里放火罪从来不判未遂的。”我听到以后快郁闷死了。
我:你这案子案情是怎么样的?
同事:.....................(未决案件,案情不便展示)。
我: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控辩审三方都要研究透《刑法》第114条的规定,而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举例和简单一刀切的标准进行认定。
当同事将这个案例向笔者吐槽该案公诉人和法官的话语时,笔者脑海中突然想起笔者父亲多年前那句“隔夜水不好、不能喝”的话语。三者的话语同样是那么带着不可否定和不可反驳的语气,可是总让人内心忿忿不平,感觉到不服。经过这些年的司法实务的经历,笔者认为之所以笔者和同事有这种忿忿不平之感,本质的原因在于:对方未抓住事物的本质,说理不透且语气强硬,有以势压人之感。
二、现有法律规定、犯罪结果的分类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现有法律规定
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该条文在我国刑法上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即:第114条规定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五个罪名。基于刑法分则条款都以是犯罪既遂为标准进行立法表述的原则,从“罪状”表述上分析,放火行为必须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才能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
那么何为“公共安全”?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是针对不特定人且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财产安全。用俗语讲就是:危及到很多旁人。虽然该观点在理论上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07号浙江江山郑小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持有此观点,因此,在本文中就该点上不做过多地谈论。
由此可见,从对《刑法》第114条规定的分析,放火罪应是一个放火行为要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危险犯,即:具体危险犯。那么,为何上文中公诉人认为《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行为犯?行为犯与危险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二)犯罪结果VS实害犯VS危险犯
笔者一直秉持着实质刑法观,一直是结果无价值论的奉行者,因此,下文论述中对于概念的解析及分类,笔者将以结果无价值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所谓的“犯罪结果”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对刑法保护的利益(法益)所造成的客观的“危险”或“损害”。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仅造成“危险”,使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处于被损害的危险状态的话,则为危险犯,如:上文中《刑法》第114条放火罪;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最终客观损害刑法保护的法益,则为实害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等。总言之,犯罪结果包括“危险结果”(危险犯)和“实害结果”(实害犯)。
“危险犯”又可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
抽象危险犯是指:立法推定的、立法拟制的、比较缓和的危险,即:立法者认为某种行为一经实施,“通常”会发生侵害法益的危险。如:《刑法》第127条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质言之,抽象危险犯可以通过生活的一般经验就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一旦实施完毕“通常”就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但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的可能性,则不可能成立抽象危险犯,如:行为人醉酒后在寥无人烟的深山老林的小道上驾驶车辆,不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危险”,则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具体危险犯是指:要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案情,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对法益已经造成了现实的、急迫的、高度的“危险”。质言之,具体危险犯是要根据具体案件不同的情形进行判断,而不是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实施完毕就达到了具体危险的程度。如:《刑法》第114条放火罪、第118条破坏电力设备罪等。
结合上文案例分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应为“具体危险犯”。就个案而言,我们要具体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了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程度,才能认定放火罪既遂与否;而不能简单的认为,放火行为实施完毕,犯罪即告既遂。
解决了犯罪结果、实害犯与危险犯之间关系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行为犯和结果犯。
(三)行为犯VS结果犯
对于“行为犯”和“结果犯”之间的区分,理论界存在重大的分歧,大致存在两种主要的观点,列举如下:
观点一:通说认为,行为犯即不存在犯罪结果,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实施完毕即告犯罪既遂;而结果犯需要出现实害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此为典型的行为无价值论者的观点。
观点二: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行为实施完毕与结果产生有无时间上的间隔。即:行为犯,行为一经实施完毕,结果(无论是危险结果还是实害结果)随之产生,双方之间没有时间间隔(或虽有间隔,但几乎同时产生);而结果犯,行为实施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产生结果(无论是危险结果还是实害结果),双方之间有明显的时间间隔。此为结果无价值论者的观点。
笔者赞同观点二的观点,其理由在于:
1.如参照观点一的观点,则无法解释上文中行为人醉酒后在寥无人烟的深山老林的小道上开车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例子。因为按照观点一的观点,依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在形式上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没有出罪的可能性。
2.持观点一者可能认为,上述例子行为人没有“社会危险性”,可以出罪。换言之,持观点一者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分两步走,即:形式上构罪+无社会危险性出罪。可问题是:一则何为“社会危险性”?这一概念本身内涵不明,外延不清,极容易在实务中被忽视和滥用,不如“法益”这一概念在具体罪名中来得清晰;二则两步走的判断模式,使得很多司法人员在第一步判断时就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而根本不会考虑第二步判断(因为第二步判断中的“社会危险性”之概念极为抽象)。
如前几年全国闻名的内蒙古王力军收购玉米案,该案原一审法院就是在两步走的判断模式上出了问题,即:原一审法院第一步判断王力军收购的行为已经符合《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形式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然后,原一审法院就没有进行第二步判断。最终导致原一审法院将无罪之人定性为有罪。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王力军改判无罪案以第97号指导案例的形式公布于社会,笔者注意到,在裁判理由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是遵循着上述两步走的判断模式,但是对于何为“社会危险性”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理由中仍然写得含糊不清,使得笔者阅读该指导案例之后,仍然处于一种朦胧的,未解惑的状态,更不用说实务中的法官和检察官。
笔者认为,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更为清晰,只需要一步判断即可,即:行为人醉酒在深山老林道路上开车,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不是危险驾驶罪的实行行为,不构成犯罪;王力军案件中,王力军的行为没有危害市场秩序的法益(国家对特定物品的垄断市场,危害到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其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实行行为的模式,不构成犯罪。
3.如果参照观点一的观点,则根本无法有效区分行为犯与危险犯,结果犯与实害犯。质言之,如参照观点一的观点,行为犯的概念与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将会高度雷同,而结果犯的概念和实害犯的概念也存在高度雷同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高度雷同后将会极易造成概念之间的混淆,在具体的运用中,让人有如坠云雾之感。
因此,笔者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行为人行为实施完毕后与产生结果之间有无时间间隔。
(四)犯罪结果VS实害犯VS危险犯VS行为犯
VS结果犯
总结上文,那么犯罪结果、实害犯、危险犯、行为犯以及结果犯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下图描述。
首先,行为犯中,抽象危险犯必然是行为犯,因为如上文所述抽象危险犯是法律拟制的危险,是根据一般常识,在行为人的行为实施完毕后“通常”会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抽象危险犯必然是行为犯。
其次,行为犯中包含部分具体危险犯,即: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形,行为人的行为一经实施完毕,就对法益产生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危险。如:在人群密集、空间狭小且周围充满易燃物的群租房中,在冬天空气干燥的情况下,行为人一旦点燃目标物,极易引起火灾,使得公共安全处于高度危险状态。那么此时,行为人点燃目标物的行为一经实施完毕,就已经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同理,部分实害犯也属于行为犯,如盗窃罪,一般情形下盗窃行为实施完毕之时,也即盗窃财物得手之时。
复次,结果犯中包含部分具体危险犯,即:行为人的行为实施完毕后,要过一段时间,其行为所造成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才能达到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程度。还是以《刑法》第114条放火罪为例,如:行为人在普通居民楼的一间房间内点火(假定无其他特殊情形),如果刚开始仅仅点燃了房间内一本书、一台电脑或者一张凳子,因火势尚未达到能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程度,不能因此而认定行为人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的既遂。(笔者认为至少要使得一个房间的物品燃烧才能构成既遂,具体既遂标准笔者下文阐述)
最后,结果犯中包含部分实害犯。如部分诈骗案件,行为人欺骗行为实施完毕后,要隔一段时间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才会打款。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上述四大概念做出上述如此的界定,才能准确判断每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正确划分四大概念之间的关系。当然,基于上述观点,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再提倡行为犯和结果犯的概念,非本文讨论的主题,另行交流。
综上,笔者认为,上文案例中公诉人、法官的观点并没有全面和正确地解读我国《刑法》第114条的规定,而究其实质原因在于:案例中的公诉人、法官没有清晰地掌握上述四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混淆了四大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了片面地判断。
三、放火罪既遂标准学说的缺陷及修正
(一)现有放火罪既遂判断标准学说的缺陷
现有学说对于《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大体总结如下:
1.物质毁坏说,即:放火的目标物的主要部分被烧毁时,放火罪就达到了既遂状态。
2.点燃说,即:放火行为开始实施之际,放火罪就达到了既遂状态。
3.独立燃烧说,即:目标物在离开引火物之后能独立燃烧,放火罪就达到了既遂状态。此观点是司法实践中大量司法机关使用的观点。
4.失控说,即:行为人失去了对火势的控制时,放火罪就达到了既遂状态。
笔者认为,上述学说的观点都未能抓住《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的本质,都是妄图以一种简单一刀切的标准进行评价。尤其是“独立燃烧说”作为所谓的通说,这种观点本质是与我国《刑法》第114条的规定相违背的,该学说以“目标物独立燃烧”就认定火势已经达到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程度,这一认定既不符合《刑法》第114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刑法》第5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常识、常情、常理,根本不能作为司法实践应遵循的标准。
(二)以“快殃及标准”修正既有学说
笔者不太喜欢某些所谓高大上、玄之又玄的理论学说,某些形而上的理论学说过于玄幻,只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硬的新名词,让人在司法实务中无所适从。
笔者认为应抓住《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的本质特征,即:火势要达到使得“公共安全”处于现实的、紧迫的、高度的危险中,才能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
有基于此,基于朴素的价值观和生活经验,笔者提出“快殃及标准”即:按照一般中立第三人的视角判断,火势有没有达到如下内心境界——天哪,快要殃及到别人了!如果达到了此种内心境界,那么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如果没有达到此种内心境界,那么不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用俗语讲,就是“城门失火有没有快要殃及池鱼”。
如上文中放火罪的例子,例一:如果在人群密集、空间狭小且周围充满易燃物的群租房中,在冬天空气干燥情况下,行为人一旦点燃目标物,一般人心中会想:一旦点燃目标物后,就会马上殃及他人。那么此时,目标物独立燃烧后,行为人的行为自然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例二:行为人在普通居民楼的一间房间内点火(假定无其他特殊情形),如果刚开始仅仅点燃了房间内一本书、一台电脑或者一张凳子时,一般人心中会想:离殃及他人还早着呢。那么此时,行为人点燃目标物且目标物独立燃烧的行为不构成《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既遂。
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刑法》第114条放火罪的本质结合生活经验,通俗易懂的“快殃及标准”能很好地区分在具体个案中第114条放火罪既未遂的状态。
(三)一司法判例之倡导
笔者注意到,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的判决已经跳脱出“独立燃烧说”的桎梏,抓住《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的本质,做出了正确的判决。
在国家法官学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主编的《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吴扬传法官在一起放火案中(案号:【2018】京0108刑初2043号)认定了被告人的犯罪处于未遂状态,其主要裁判理由认为:
(1)《刑法》第114条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其既遂的标准不仅要引起放火对象的独立燃烧,同时火势应当具备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火灾的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
(2)如果认为只要点燃放火对象就是既遂,则等于完全排除点火之后行为人构成未遂或者中止的可能性,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3)判断点火之后是否具备未遂的可能性,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结合火势已经造成的损害大小,现场人员施救的可能性,放火对象物的具体情况,引燃物的种类和数量,气温气候等各种因素;
(4)在易燃易爆物众多的现场,只要行为人点着明火,火势极有可能迅速蔓延,造成重大损害,此时不存在点火后未遂的可能性。笔者对该法官的学术水平、说理逻辑及裁判的勇气深表敬意。笔者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学术能力的法官,有担当的法官裁判出更多说理透彻的,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综上,笔者认为,理论学说不能脱离现有法律规定,否则就有“法外立法”的嫌疑,并且不符合《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学说理论也不能脱离生活常识,毕竟我们的法律要运用到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案例中。脱离了法律、脱离了生活常识的理论学说,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最后只剩下创造者的孤芳自赏罢了。
四、抓住本质,说理透彻,防止以势压人,防止简单一刀切
(一)“隔夜水”不能喝的真相
回归到上文那杯“隔夜水”,笔者后来查询了大量为何“隔夜水”不能喝的资料。最科学说法认为,“隔夜水”之所以不能喝,是因为防止傍晚有昆虫或者灰尘在人们休息的时候落入水中,使得水中充满细菌。换言之,如果能保障水杯的密封性,那么“隔夜水”是可以饮用的;另外,水烧开后,水中的亚硝酸物质会变得很少,即便搁置很长时间,在水杯密封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
读到此以后,笔者认为,自己的父亲并未抓住事物的本质,而是遵循一条简单粗暴的道理“隔夜水不好、不能喝”,就将笔者前一晚倒满的水杯清空。当然,笔者认为,父亲出发点是为笔者好,但是其简单粗暴的说理,确实令笔者心有不忿。
(二)司法实务中的“隔夜水”
然而,遗憾的是,笔者发现,我们司法实务中充斥着这种“隔夜水”,就如上文中笔者同事的案件一样。什么“我们都这么判的”、“我们都这么认定的”、“合伙人就不是从犯”、“电话传唤就不是自首”等等。简单的标准、粗暴的说理,似乎成了司法实践中某些检法人员的标配。他们看似依法办案,铁面无私,实则未抓住事物的本质,最终导致裁判结果谬之千里。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做法埋下了当事人怨恨的种子,也埋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如上文那一杯令人忿忿不平的“隔夜水”一样。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2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说明量刑建议的理由和依据。”但是在实务中,我们如何践行该条款,仍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我们以后的司法实务中,少一点滞闷苦涩的“隔夜水”,多一点清爽甘甜的“山泉水”,让这一丝清甜能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